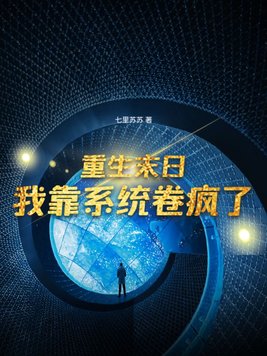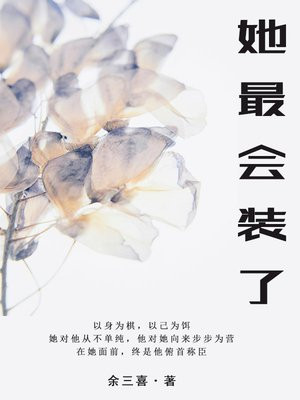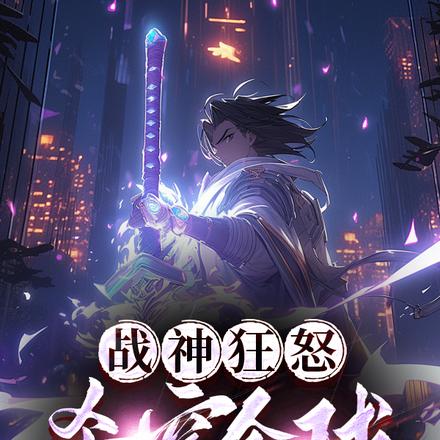首发:~第3章 战守之争
“看清楚了,又能如何?”刘禅还未从胡氏那边转过神来,含混回答,挥手又要下笔。
“皇上,这一次不比往常呀!”蒋琬急又解释。
刘禅这才放下朱笔,拿起相父的表章细看。这一次确实不比往常。相父奏的不是旁人的事,而是他要自贬三级。
刘禅立刻险上写满了难色。以往凡是相父的表章,不论什么事,他都是有求必应,有奏必准。他知道相父一切早都安排好了,才来向他上奏,他不过是写个“准”字钦定而已。现在相父要自贬三级,这可怎么办呢?贬了丞相,谁来治理军国大事,而他又怎么敢贬相父之职呢?
这是他做皇帝以来,第一次自己拿主意。又是这么难拿的主意,真把他难死了。
“蒋爱卿,你说这表章,是准还是不准?”刘禅苦着脸向蒋琬讨主意。
蒋琬也不敢乱作主张。丞相自贬,乃是国家第一等大事。再者,丞相虽然诚心自责,众将士一定心中不允。
贬了他们的统帅,就等于一笔抹煞了他们所有的战功。他们虽然无功而返,但毕竟还是饮马渭水,兵困秦川,杀得魏军首尾不能相顾。
丞相上表自贬,他们一定以为,这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,朝延断然不敢准旨,反而还要降旨好言相慰呢!
然而丞相之心,他最清楚。丞相所求的不是眼前得失,而是光汉复刘的一统大业。丞相这么做也实在是用心良苦,他要实现这个宏愿,就必须功过分明,赏罚严明,律人必先责己,从自己做起,这样才能号召天下。
蒋琬以为这么大的事情,他个人不能轻率表态,应该由大臣朝议而定,才能不失偏颇。
自从丞相出师以来,刘禅已经很久没有设朝议事。朝钟一响,总摄官中诸事的侍中郭攸之、董允、费祎,总督御林军马的大将向宠,掌丞相府事的长史蒋琬、张裔,谏议大夫杜琼,尚书杜微、杨洪,太史谯周等内外文武官员一百余人,齐聚承明殿。
他们都是经过孔明挑选出来的能臣,留在成都总理宫中之事和丞相府事。
听到丞相上表自贬三级的议题,朝臣们也都面有难色,没有人敢轻易发言,承明殿内鸦雀无声。
侍中费祎向来直言不讳,敢作敢当,如何忍受得了如此沉默,便首开议论,打破寂静。他说:
“丞相治国治军,必以奉法为重,法若不行,何以服人。此次北伐失利,丞相自贬,上合礼法,下服人心,可以准旨。”
费祎准则一定,朝臣议论起来,也就不怕有失偏颇。
他们虽然都同意准旨之议,但是措词多是赞扬丞相公而忘私,赏罚分明,宽严有度,败中也有不败的好话。
特别是对丞相神机妙算,智取三郡,以“空城计”抚琴吓退司马懿等几处成功之举,众臣无不佩服,个个津津乐道。竟没有一个人对丞相贬职以后,朝政会有什么影响,军中将士会有什么反应,对未来的光复大业会起什么作用等等,进行认真的分析。
刘禅耳听众臣纷呶无休的赞扬之声,心里却在担忧谁来代替丞相。他以为相父自贬以后,就必须另封一个丞相替他管事。
他睁大眼睛在殿上百余文武官员中扫来扫去,这些能臣,不是相父的门生故旧,就是相父先后举荐的人才,他们谁能接替相父管事呢?他更拿不定主意。
刘禅把他的担忧一说出来,堂上立刻一片哗然。后主真是憨直过了头,全然不会转弯。丞相自贬,不能不准,但是丞相自贬之后还是丞相,谁敢代替丞相呢?
费祎见后主那付愁眉苦脸的样子,急奏道:
“丞相不过是用人失误,失守街亭,这才导致北伐失利。主要的责任是马谡。丞相自贬,实乃高风亮节,只能贬其职,不能夺其位。”
刘禅听了,还是不明其意。侍中董允赶紧解释道:
“费祎之意,就是请皇上准了丞相自贬之请,但请丞相仍行丞相之事,照旧总督人马。丞相只是暂贬丞相之职,丞相还是丞相。”
刘禅这才明白,不由大喜。即令费祎到汉中下诏:贬孔明为右将军,行丞相事,照旧总督一切军马。
朝议方定,忽然太史谯周出班奏道:
“臣以为,贬不贬丞相之职,实乃小事,知不知北伐失败原因,却是大事。丞相之误,不是用人之误,是战守方略之误,丞相本来就不该出兵,请皇上明鉴。“
谯周总是别出心裁,所论与众不同。
丞相北伐之初,曾上《出师表),后主召群臣议论,谯周就极力反对用兵,说是夜观天象,北方旺气正盛,星曜倍明,不是时机。
但他一向不曾参与政事,不过是一个掌管祭礼和记事的太史,谁会相信他的话呢?
现在丞相虽然兵败,但这明明是马谡失守街亭所致,他又说成是丞相战守方略之误。
众臣早知他的秉性,听了见怪不怪,也不与他争辩。
谯周见众臣听了他的话无动于衷,反而更加激动。放开又尖又细的嗓音,对谏议大夫杜琼吼道:
”你是言官,为什么一言不发?&34;
杜琼只是微笑,却不与他计较。
谯周更加冲动,他以为战守方略的选择,事关国家生死存亡,不可不论清楚。谯周见杜琼不理睬他,又对尚书杜微、杨洪大声贵问:
“你们是掌管朝廷机密的人,难道也不知内情,为什么都不说一句实话?&34;
”你怎么像个疯子!“杜微、杨洪却不让步,齐声回敬了一句。”什么?我是疯子?哈哈。“谯周又对三位侍中和两位留府长史大喊:”你们都是朝中权臣,也都是丞相的左膀右臂,现在我只问你们一句话。假如马谡不失街亭,丞相在关中用兵,又能坚持多久?&34;
几位权臣见问,竟都怔住,回答不出来。
蒋琬是筹集北伐军需的总管,国中人力、财力之困,筹备军需之难,心中最明白。他早感到丞相此次用兵,实是勉为其难。谯周所问的,的确是要害。假如马谡不败,坚守街亭,关中之战能否坚持下去,实不可知。
但是光汉复刘大业,是蜀汉君臣的神圣职责,偏安自守,等待挨打也不是上策。
丞相兵败,原因很多,到底北伐是不是时机不合,或者该不该用兵,都不是他们这些人所能研究明白的事。便对谯周心平气和答道:
“你不在其位,不知其政,是战是守,丞相比你清楚得多。”谯周听了更不服气,正要发话,后主急忙喝住。他说他做皇上的都不敢怀疑丞相的忠心和谋略,你一个小太史,就不必多心了。自他登基以来,从来是“政由相父、祭则寡人”,这个原则今后也不能变。
谯周见责,口虽不言,心中仍然不服气,轻叹道:为何朝中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呢?
3
费祎主张准了丞相自贬,实是出于公心,现在派他前往汉中宣诏,心里却十分为难。
论派系,他还是刘璋旧人,刘璋之母还是他的姑祖母。但是丞相对他十分器重,对他屡加提拔重用。
几年前他还是黄门侍郎,众臣之中,他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官。丞相平南中凯旋班师,他随众臣出都门数十里迎接。丞相竟独请他上车同载,沿途接受众臣的迎拜,直入都城,让群臣见其之重。
后来又以他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,让他大展其才,不辱使命,又让朝野刮目相看。
此次北伐前夕,又迁他为侍中,成为皇上管理国政的助手。位高权大,一跃成为朝中权臣之一。他和另外二个侍中和留府长史蒋琬等人,实际上是代理丞相之职,统筹军国大事。
对于这样尽心栽培自己的恩师,现在让他当面颁诏贬其三级,实是打不破情面,难以开口。
他对丞相确实是从心里佩服,敬其忠心耿耿,慕其大智大勇,仰其丰功伟绩。出征之前,那一篇《出师表),就令他读得心潮彭湃,热泪盈眶。
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。二十一年来,为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。夙夜忧叹,唯恐托付之不效。 &34;
字里行间,可见丞相呕心沥血,把心操碎。
这次他之所以主张准了丞相自贬,也是从国事出发,大胆进言。若论私情,他应该力保丞相无罪才是。但他是丞相所器重的人,他不能因私废了国法,令丞相失望。
行前,他还特地拜访了留府长史蒋琬。蒋琬奉旨劳师,刚从汉中回来,最知道丞相此时的情绪。他向蒋琬请教,应该如何劝慰,才能使丞相不感羞恚,使军中将士无怨无恨。
蒋琬却只是说,丞相之心,清如明镜,不是言语所能劝慰,这话更令他感到此行之尴尬。
进入汉中,只见大军营盘星罗棋布,散落在高坡平地之中。栅寨整齐,旗号鲜明,号角此起彼落。将士们有的在练武,有的在耕作,有的在打造攻城渡水之器。六军散而不乱,忙而有序。一路之上,竟没有看见一个闲散的人。
费祎在马上,越是钦佩丞相治军之能,越是感到见了丞相,难
以开口宣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