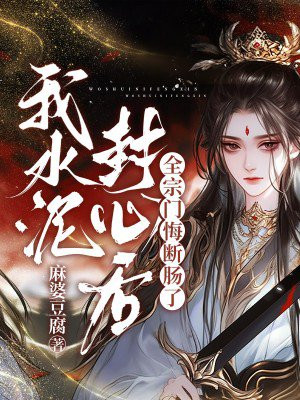首发:~第49章 落子勿言悔(1)
霍光走后,刘询就开始削减霍家的势力,去霍成君处越来越少,直到最后绝迹于椒房殿。
霍光死后的第二年,刘询准备妥当一切后,发动了雷霆攻势,开始详查许平君死因,医婆单衍招供出与霍氏合谋,毒杀了许皇后。霍禹、霍山、霍云被逼无奈,企图反击,事败后,被刘询以谋反罪打入天牢,霍氏一族其他人等也都获罪伏诛。霍成君被夺去后位,贬入冷宫。当年权势遮天、门客遍及朝野的霍家,转眼间,就只剩了霍成君一人。
刘询的心腹大患终被拔除干净,随着霍氏的倒台,皇权的回归,两个新兴的权力集团隐隐浮出水面,一个是藏于暗处的宦官集团,以何小七等贴身服侍刘询的宦官为首;一个就是刘询亲手训练出的“黑衣军”,他们掌握了禁军、羽林营,甚至军队。表面上看起来,黑衣军和宦官是刘询的左膀右臂,一明一暗,应该齐心合作,可何小七总觉得黑衣人看他的眼光透着怪异,他总会不自禁地想起那帮被他活埋了的黑衣人,常常大夏天的,惊出一身冷汗。
孟珏对刘询下一步的动作了然于胸,刘询知道他了然于胸,他也 知道刘询知道他的了然于胸,彼此都明白他们两个这局棋下到此,已经要图穷匕现,但是两个人依旧君是明君,臣是贤臣,客气有礼地演着戏。
孟珏在霍光病逝不久的时候,就向刘询请求辞去官职,刘询收下了奏章,却没有回答他,只是下令把一品居抄了,将老板打入了天牢。第二日,刘询亲手训练出的“黑衣军”开始查封城里各处的当铺,搜捕抓人。获罪的罪名,何小七自会网罗,他现在熟读大汉律典,对这些事情很是得心应手,一条条罪名安上去,可谓冠冕堂皇,罪名确凿。第三日,孟珏向刘询要回了辞呈。
之后,长安城内的商铺不几日就会关门一家,或倒闭一家。
刘询每次收到何小七的密报,总是无甚喜怒,何小七却是每奏一次,就心寒一次,这些关门的商铺全是刘询已经知道的,孟珏这样做,究竟是向刘询示弱,还是讥讽刘询?孟珏又是如何知道他已经查出这些商铺的?
等何小七名单上的商铺倒闭得差不多时,一日,孟珏给刘奭上完课,微笑着对他说:“这些年,我能教给殿下的东西已经全部教完。”
刘奭听后,手慢慢地蜷到了一起,力持镇静地问:“太傅也要离开了吗?”
孟珏没有回答,只微笑着说:“你的父皇与你性格不同,政见亦不同,你日后不要当面顶撞他,他虽然待你与其他皇子不同,可天底下最善变的是人心。”
刘奭抿着唇,倔强地说:“我不怕他!”
孟珏未再多说,起身要走,刘奭站起来想去送他,孟珏道:“我想一个人走一走,你不必相送了。”
刘奭虽贵为太子,可自小跟随孟珏,见他的时间远远多过父皇,对他有仰慕、有尊敬、有信任,还有畏惧。听到他的拒绝,只能停下来,站在门口,依依不舍地望着孟珏背影。
待孟珏的身影消失后,他正要转身进屋,却发现孟珏惯配的玉珏遗落在地上,连忙捡起,去追孟珏。
孟珏快到前殿时,看到刘询一身便袍,负手而立,观河赏景,恰恰挡住了他的路。
孟珏过去行礼,“陛下。”
刘询抬手让他起来,却又一句话不说,孟珏也微笑地静站着。有宫女经过,看到他们忙上来行礼,袖带轻扬间,隐隐的清香。
刘询恍惚了一瞬,问道:“淋池的低光荷开了?”橙儿低着头应道:“是!这几日花开得正好,太皇太后娘娘赏赐了奴婢两株荷花。”刘询沉默着不说话,一会儿后,挥了挥手,让橙儿退下。
不远处,沧河的水声滔滔。刘询对孟珏说:“这些年,我是孤家寡人,你怎么也形单影只呢?”孟珏微笑着说:“陛下有后宫佳丽,还有儿子,怎么能算孤家寡人?”
刘询没什么表情地问:“你对广陵王怎么想?”
孟珏淡淡说:“一个庸才,不足为虑。”
刘询点了点头,正是他所想,这种人留着,是百好无一坏。
孟珏却又紧接着问:“臣记得他喜欢驯养桀犬,不知道现在还养吗?”
刘询眉头微不可见地一蹙,深盯了眼孟珏,孟珏却是淡淡笑着,好似什么都没说。
好半晌后,刘询淡声问:“你我毕竟相交一场,你还有什么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吗?朕可以替你完成。”
孟珏笑:“我这人向来喜欢亲力亲为。”
刘询也笑:“那你去吧!”
孟珏微欠了下身子告退,不过未从正路走,而是快速地向沧河行去,刘询刚想出声叫住他,孟珏一面大步走,一面问:“你可还记得多年前的沧河冰面?你我联手的那场血战!”
刘询呆了一下,说道:“记得!平君后来询问过我无数次,我们 是如何救的她和云歌。”
“你去找刘弗陵时,也杀了不少侍卫吧?”
刘询微笑,“绝不会比你的少!”
……
隐藏在暗处的何小七看预订的计划出了意外,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,本想派人去请示一下刘询,可是看孟珏直到此刻,都还一副从容自若、谈笑风生的样子,他的愤怒到了顶点,黑子哥他们碎裂的尸体在他眼前徘徊,淋漓的鲜血直冲着他的脑门。
隐忍多年,终于等到这一日,不能再等!以孟珏的能耐,出了这个皇宫,就是刘询也没有把握一定能置他于死地。何小七向潜伏在四周的弓箭手点了点头,率先将自己手中的弓箭拉满,对着孟珏的后背,将盈满他刻骨仇恨的箭射出。
一箭当先,十几只箭紧随其后,孟珏听到箭声,猛然回身,一面急速地向沧河退去,一面挥掌挡箭,可是利箭纷纷不绝,避开了第一轮的箭,却没有避开第二轮的,十几只箭钉入了他的胸膛,瞬间,他的前胸就插满了羽箭,鲜血染红衣袍。
刘询负手而立,站在远处,淡淡地看着他,他也看着刘询。沉默中,他们的视线仍在交锋,无声地落下这局棋的最后一颗子。
刘询的眼睛内无甚欢欣,只是冷漠地陈述一个事实,“我们终于下完了一直没有下完的棋,我赢了。”孟珏的眼睛内亦无悲伤,只有淡然的嘲讽,“是吗?”
淡然的嘲讽下,是三分疲惫、三分厌倦、四分的不在乎。他的身体摇摇晃晃,再站不稳,剧痛让他的眼前开始模糊不清,刘询的身影淡去,一个绿衣人笑着向他走来。他的唇畔忽然抿着丝微笑,看向了高远辽阔的蓝天。在这纷扰红尘之外,悠悠白云的尽处,她是否已经忘记了一切,寻觅到了她的宁静?
她真的将我全部遗忘了吗?她的病可有好一些?今生今世不可求,那么只能修来生来世了……
他的身体向后倒去,身后正是滔滔沧河,身体入水,连水花都未溅起,就被卷得没有了踪影。
何小七轻声下令,隐藏在暗处的宦官迅速消失不见,一丝痕迹都未留下。一群侍卫此时才赶到,刘询下令:“封锁河道,搜寻刺客尸体。”
张安世和张贺气喘吁吁地赶到,也不知道张贺脸上的究竟是汗水还是泪水,他刚想说话,被张安世一把按住,拖着他跪了下去。
张安世恭敬地说:“陛下,沧河水直通渭河,渭河水连黄河,长安水道复杂,张贺却很熟悉,不如就让张贺带人去搜。”
刘询对张贺的信赖不同常人,闻言,点头说:“张爱卿,你领兵去办,此事不要声张,只向朕来回报。”
张贺呆了一瞬,反应过来,忙磕头接旨。起身后,一边擦汗,一边领着兵沿沧河而去。
张安世这才又磕头向刘询请罪,“听闻霍家余孽袭击陛下,臣等护驾来迟,有罪!”
刘询却半晌没说话,张安世偷偷抬眼看,发觉刘询的眼睛正盯着侧面。张安世将低着的头微不可见地转了个角度,看见不远处的雕栏玉砌间,站着太子刘奭,他眼中似有泪光,看见刘询,却一直不上前行礼,甚至连头都不低,毫不避讳地盯着刘询。一会儿后,他突然转身飞快地跑掉了。
张安世不敢再看,额头贴着地,恭恭敬敬地跪好。
半晌后,张安世看见刘询的袍子摆飘动起来,向远处移去,冷漠的声音从高处传来,“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刘询向前殿走去,走到殿外,看到空荡荡的大殿却恍惚了,我来这里干什么?大臣们早已散朝了!
随意换了个方向走,看到宣室殿的殿宇,想起那也是座空殿,只有一堆又一堆的奏折等着他,可是他现在难以言喻的疲惫,只想找个舒适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会儿。
他又换了个方向,走了几步,发觉是去过千百次的椒房殿,虽然已是一座空殿,他心头仍是一阵厌恶,转身就离开。
刘询左看右看,竟然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未央宫,未央宫!说什么长乐未央?这么多的宫殿,竟然连一座能让他平静踏实地休息一会儿的宫殿都找不到。
不知不觉中,他走出了未央宫。
大街上熙熙攘攘、人来人往,商铺的生意兴旺,人们的口袋中有钱,似乎人人都在笑。田埂上,是荷锄归家的农人,还有牧牛归来的牧童,杨树皮做的简陋笛子,吹着走调的欢乐,看到刘询,牧童大大咧咧地腾出一只手,指指路边,示意他让路,刘询也真就退让到一边,让牧童和牛群先行。袅袅炊烟下,竹篱茅屋前,妇人正给鸡喂最后一顿食,一边不时地抬头眺望着路的尽头,查看丈夫有没有到家,看到刘询盯着她发呆,她本想恼火地呵斥,却又发现他的目光似看着自己,实际眼中全是茫然,妇人以为是思家的游子,遂只扭转了身子,匆匆进屋。